

敦煌,一个藏着无尽故事和传奇的地方,它静静地镶嵌在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见证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记录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审美变迁。
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敦煌》立足于史实,驰骋于想象,以唐代贞观年间为时间背景,以李世民的御用画师祁希为主线人物,描绘了王朝征战、僧俗开窟、宫廷画师造像的故事;以瓜州、沙州为空间背景,书写了敦煌的历史变迁和民族融合;同时加入现代元素,通过一位吐谷浑后裔的人生连接古今,让敦煌变成贯穿古今的人间道场。近日,本报记者对陈继明进行了专访。
“《敦煌》的诞生凝结了我对西北这片土地深沉的情感和长久以来的思考”
记者:《敦煌》已不是您第一次将创作视角聚焦西北,促使您创作这部小说的契机是什么?
陈继明:7年前,我的长篇小说《七步镇》出版后,责编建议我继续以西北为背景创作。经过深思熟虑,我认为敦煌作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其历史复杂性和文化丰富性值得深入探索。
其次,《敦煌》的创作让我有机会延续《七步镇》中未尽的故事线,比如将人物令狐昌引入《敦煌》,进一步展开他的故事。所以,《七步镇》结束的地方,正是《敦煌》开始的地方。
另一个激发我创作《敦煌》的原因是我长期以来对吐谷浑这一古代族群的兴趣。我是甘肃天水甘谷县人,甘谷县古称冀县,又叫伏羌县。历史记载,吐谷浑人从阴山往西迁徙的过程中,第一站到了陇山山脉的腹地,也就是甘谷县一带。早在30年前,我在查阅甘谷的文史资料时,就经常看到关于吐谷浑人的故事。
吐谷浑人聚居于甘谷的历史,是展现我国丝绸之路沿线多民族交流融合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的生动例证。在小说《敦煌》中,我以吐谷浑人来敦煌天水村的故事线,描述了吐谷浑人和汉人的交流往来。通过这些细节故事,读者可以看到,在历史长河中,各民族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格局。
记者:小说《敦煌》映射了敦煌千年不息的文化和精神传承,勾勒出一幅穿越时空的历史画卷。您在写作前做了哪些准备呢?
陈继明:写这样一个题材,确实需要做大量功课。首先是要让自己成为半个行家。比如对开窟、画像的技术,主画师和协助者如何合作等知识,都要逐一了解。另外就是搜集资料,我大概看了200多本关于敦煌的书籍和大量相关史料,这些都是我写作的基础。
不过,即便做了很多准备,写作还是充满不确定性。在我看来,创作者就像一个探险家,开始写作时,探险就开始了。作品没有完成,作者自己也不知道最终模样,我就是带着这样的理念来创作《敦煌》的。
在我看来,《敦煌》是我目前写过的最为丰厚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我最有原创性、发挥最为充分的一部小说。我将自己在西北40多年的生活记忆与积累倾注其中。可以说,《敦煌》的诞生,凝结了我对西北这片土地深沉的情感和长久以来的思考。
“写出一个丰富多义、难以被简单归纳和言说的敦煌”
记者:有关敦煌的书籍种类繁多,从知识普及到理论研究,再到非虚构作品等,不一而足。您想写的又是一个怎样的敦煌?
陈继明:在构思这部作品之初,我为自己设定了两点“不写”。第一,不直接描写藏经洞的故事,因为这个题材已经被广泛探讨,很难再有新的突破;第二,不将敦煌视为一种已经固化、只供人瞻仰的历史符号和文化象征,而是希望展现一个变化的、充满活力的敦煌。
我也定下两点“要写”。一是聚焦人物,展现人类在面对自然与文化时所表现出的力量和智慧,确立人在叙事中的主体地位。二是赋予动物更加丰富的角色意义。在《敦煌》中,马、骆驼等动物不是工具或背景,而是与人类共同构成这个复杂而生动世界的重要部分。
小说中,鸣沙山的一面是千佛洞,另一面就是一个狼窝,狼窝旁边又是羊冢。强和弱、善和恶、生和死,就这样在敦煌相依相存。我希望写出一个丰富多义、难以被简单归纳和言说的敦煌,给读者展现一个富有想象力的空间。
记者:千佛洞里人语响。在您笔下,敦煌从一个知识性的文化遗存变得血肉丰满。在叙事上,您为何选择宫廷画师祁希(后改名雪祁)作为主人公?
陈继明:我对石窟很感兴趣,画师便是一个合适的视角,能够将相关内容有机地串联起来。小说中,祁希12岁便成为阎立本的弟子,后来成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宫廷画师,并随其南征北战。通过他的眼睛看敦煌,实际上也是从庙堂的角度审视这个世界。
祁希曾三次进入敦煌,第一次去是学画和搜集情报;第二次去是开窟造像,画壁画;第三次去是寻找诅咒窟的谜底并定居。祁希这一虚构的人物及其经历,以敦煌为中心,不仅有效地架起了庙堂与民间之间的桥梁,更串联起东西方交往故事。
总之,借助祁希这个人物,我希望深入敦煌的内在肌理,探索那个时代的人是如何生活的,揭示出一个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敦煌。
“我把敦煌当镜子,为的是照见人间的图景”
记者:在小说中,您以恢弘大气又细腻缜密的语言,写出了敦煌的历史文化和精神气象,您如何看待小说创作中语言的作用?
陈继明:语言不仅是表达的工具,更是作品的内容和灵魂。它是一个复杂的体系,蕴含着紧张、松弛、速度、张力、深度及悬念等多种元素。一名优秀的作家,需要具备灵活的语言表达能力。在创作中,我一直追求语言内部的代入感,努力将读者引入其中。在《敦煌》这部书中,我尝试将普通话与甘肃方言相融合,期待为语言注入一种新的营养和活力。
我相信,通过精心雕琢的语言,可以使小说引人入胜。
记者:作家邱华栋认为,《敦煌》之所以能成为一部具有大气象、大格局的作品,正是因为作家拥有深刻的文明思考。您认为,这种“深刻的文明思考”体现在什么地方?
陈继明:小说通过多条并行的故事线,展现出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图景。吐谷浑人在敦煌天水村不断开拓生存空间的故事,展现了族群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汉人后裔令狐昌一家的日常生活和造窟故事,展示了一个普通家庭在历史变迁中的命运起伏,进一步凸显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
同时,我也想让这部小说具有当代感,在语调、趣味、观照方式以及叙事手法上都更有当代小说的味道。通过“我”与吐谷浑后代慕思明这两个角色的存在,小说得以超越故事层面,更深入地探讨文化传承、历史记忆等主题。这些主题不仅贯穿于古代故事之中,也在现代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在创作中,我把敦煌当镜子,为的是照见人间的图景。书中的人物和情节实际上是对敦煌这一独特地域文化的“映射”。无论是汉人、吐谷浑人还是粟特人,都在与敦煌这片神奇土地的相遇中,激发出各自的性格特征和生命特质。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各有特色,但实际上早已融为一体。正是像敦煌这样的中华大地的自然环境及文化氛围,使这些人物密切联系并塑造其共同的内在品质。这种联系在漫长的岁月里不断发展、深化,推动中华民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编辑:魏妙)- 前一则: 弦歌不辍 古今共鸣——“传统@现代 民族音乐文化展”在京开展
- 后一则: 《敦煌》赏读(节选)
最新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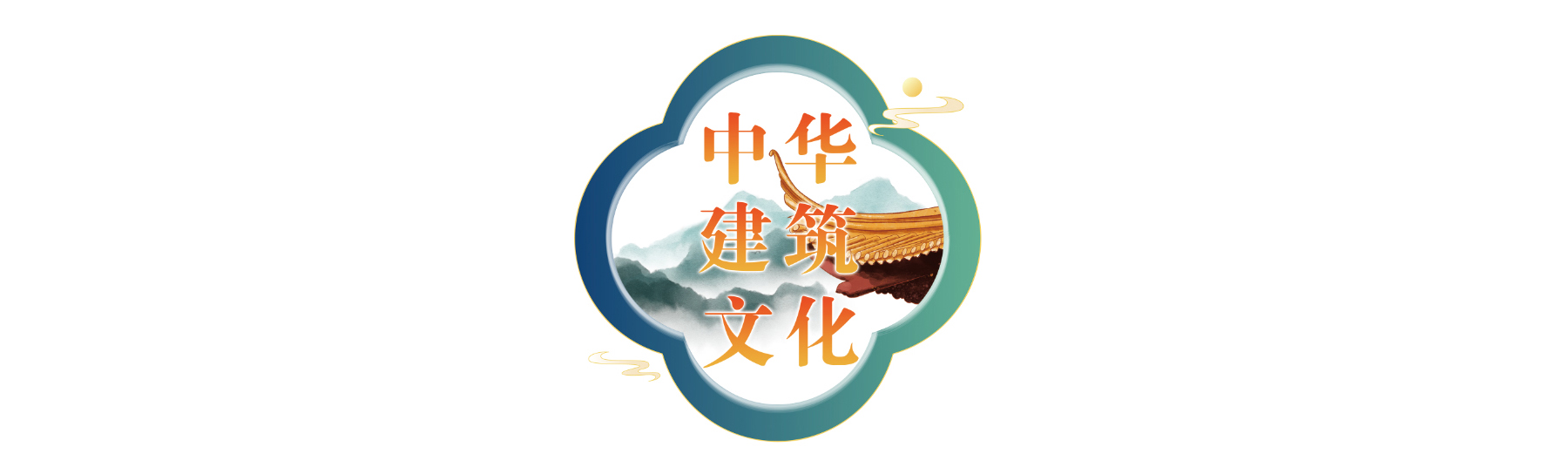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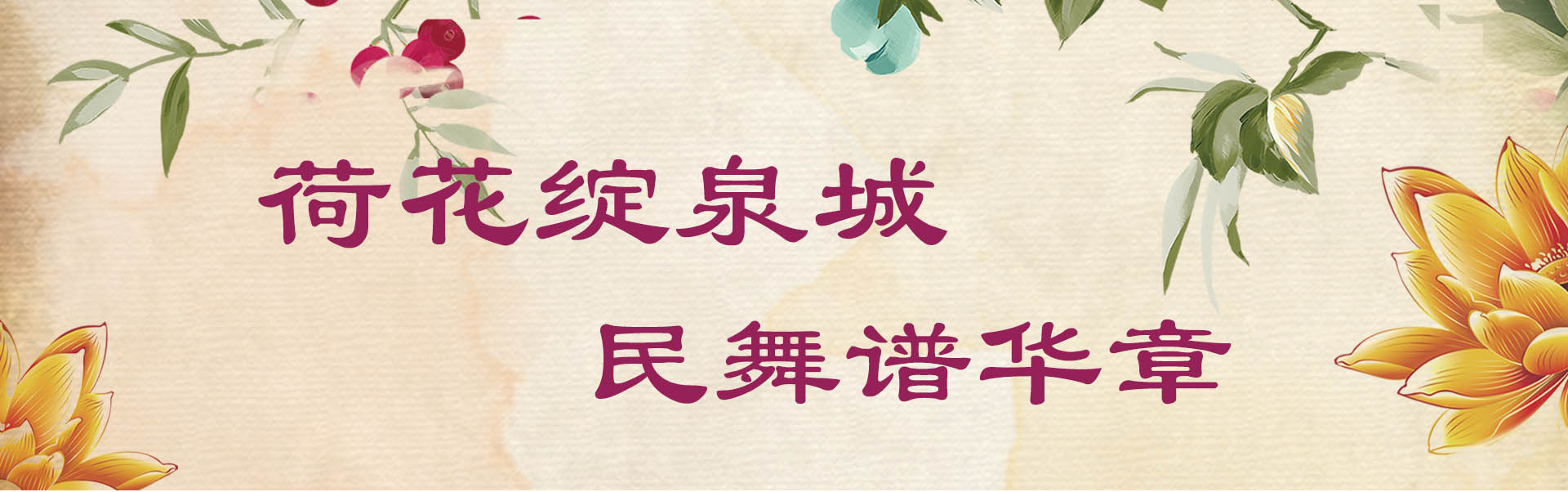
 zgmzzjw@sina.com
zgmzzjw@sina.com 